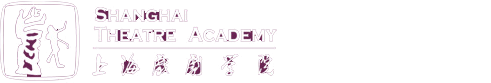10月21日下午,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在我校红楼209教室为听众们做了一场题为《非遗与灵感:女书的创作过程》的精彩讲座。
讲座开始,谭盾先谈论了关于艺术的追求。首先便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永远比别人给你的高。并且引用了《列宁与音乐》的一句话,如果你还年轻,还相当艺术家,那就把自己当做艺术家。第二点需要的是自由,接下来是勇敢,最后便学会从自己的作品中脱离出来,学会以一个陌生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如同庄周梦晓迷蝴蝶般,有进入,也有超脱。并给与了一个新名词Timing——心理时间的刻度,让我们可以丈量自己与作品的距离。
讲座进入主题,谭盾给听众讲述了《女书》的由来。那是他在夜晚神游台北,在诚品书店的美丽邂逅。传说五十年代初,共和国刚成立,一群女人要看毛主席,后因语言不通,竟被当做精神病,送进了精神病院。便是这么一段小小的序言,引起了谭盾对于女书的兴趣,开始了对女书的调查、了解。那么女书是什么呢?那是仅在女人之间流传的语言,以口口相传和吟唱的方式传承,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并且有专属的文字,主要写于女生的私密物件上,如扇子、手绢、肩带。内容多以女生对于男生的了解、好感、爱慕为主,被戏称为“女人的圣经”。那么男人眼中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呢?谭盾联想到了乐器中的竖琴,那和男人眼中的女人很接近,只是一种装饰美,拥有华丽的外表、色彩,但其本身的旋律感并不是很强,常被忽略不计,仅作为配乐在演出中出现。那么女书的出现相当于对于竖琴的重新认识,谭盾想要使它具有强烈的叙述性和戏剧性,成为作品中的一个主角。谭盾自称《女书》是微电影交响诗,有人疑问,他是如何将一个民族的东西拍的那么优雅、浪漫。而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便是电影手法,谭盾最初对于拍摄的想象是一个镜头一部电影,结果最后达到了出人意料的宁静效果。对此他如是解释到,一个镜头相当于一根琴弦,一部电影便是一张白纸,一个空间,这两者的结合,呈现出的便是这样一种宁静悠远的浪漫。在整个讲座中另一个被反复提到的重点便是对位,他说对位是谐和的最高。为了便于理解,将中国国歌与美国国歌的开头前三个音进行对比,分别是do mi so 和so mi do 这样完全相反的两种,但是一旦将其结合,竟然成为了动听的音乐。
关于女书的研究是有派别的,第一派觉得它是明末清初,女人权利受限而在女人之间发明流传的语言文字。另一派则觉得女书一直存在,从有甲骨文,音乐的时代便已经拥有。谭盾在调查的途中发现一个村庄,在坚守了很久之后意外从当地的一位女歌神口中感知到了女书的音乐,其音乐保留了最原始的狩猎、求偶时特有的节奏,与心跳相近,全是三全音,与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完全不同。另外便是女书文字本身的不同,它避免了一切方块字的横平竖直,浑然天成的自成一派,为电影找到了最好的原型。在电影的音乐方面,谭盾说,器乐创作与歌曲创作是不同的,西方是乐音的体系,而中国则是有机的方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体系。
讲座的最后是提问环节,听众们踊跃提问,与谭盾就文化与创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文:叶韵 图:顾秋梦 编辑:榕树)

图为谭盾先生在做讲座

图为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图为听众提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