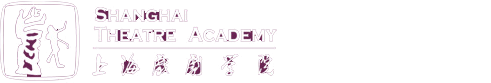|
| 宋光祖 1939.4-2013.9.1 生于上海 |
2013年9月1日20时08分,敬爱的宋光祖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4岁。9月2日上午,他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没有了病痛的折磨,宋老师的在面庞安静、舒展,仿佛从他那张旧照片上走了下来��那上面的他,年轻、俊秀,爽朗地笑着。这种爽朗的笑,在他的学生们的回忆中,在他们相处的岁月里,是绝不多见,但也不缺乏的。它常常并不发生在学术讨论时,那时的宋老师是严谨甚至严肃的,它多半发生在课下与师生用餐或闲聊时。只有在这时,学生们才会发现,一头白发、书卷气极重的宋老师,也有一颗年青、跳动的心。也就在这时,熟悉他的才发现,笼罩着宋老师的安静,不是陈陈暮气,不是横秋的老气,而是一种谦谦君子风,一股淡淡的书生气。
先来看一段宋老师的简介:
宋光祖,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戏曲学“戏曲创作理论研究”博士生导师从教二十余年,悉心钻研区别于话剧的戏曲创作理论。从现当代戏曲创作的实际出发,上溯古代而明传统之继承革新,外考西洋而树民族之独特体系。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创设起讲、练结合的“戏曲编剧理论与写作”课,本课获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奖,另获2001年上海市育才奖、首届上海市高校名师奖。所撰教材和论著有:《戏曲写作教程》、《戏曲写作论》、《中国戏曲名著选读》(两主编之一)、《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主要撰稿人之一)、《话剧之友手册》(主要作者)和《“红楼”戏曲概述》等。另有戏曲剧本多种发表或上演。
看到这样的介绍,对宋光祖教授会生出一些敬畏,然而,宋师与其说可畏,不如说可敬。一个人有了才华或者有了贡献,倒是可以对周围的人有些不屑和怒目的。而宋老师却绝非如此,他更像一位古典温文尔雅的书生,他的个性只灌注于他的文字中,即便是他的文字,意思不妨尖锐,而行文却仍是娓娓道来、从容舒展的。
据他的亲属回忆,宋老师的父母在世时,他便赡养双亲,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兄弟姐妹也十分关心,是一位受家族中小辈非常尊敬的长者。
他带过的学生曾写文章纪念、追忆在校时与宋老师交往的诸事,内中写到他送了一瓶湖南辣椒给宋老师,结果宋老师嘴上起了泡,代表他“付出了一些努力并有了代价”。之后,在这位同学午休时,宋老师原物奉还,并且悄声说:“原礼奉还这是不礼貌的,但你家乡的这些好东西,对于在上海生活的你,不是更重要么。”陌生的读者见到此语,或许会粲然一笑,对于熟知宋老师的学生、同事,未免要鼻子为之一酸了。这正是宋老师,严谨而又不失温和,严肃却又不乏体贴。至于宋老师的“原物奉还”,遇到的不止这位仁兄一人。有位同学,曾经送了宋老师一套可作为资料研究的地方戏碟片,然而在宋老师患病后,他细心地将看过的碟片包好,重新送给了这位同学。送东西的人或许已经忘了,可他还时时记得,这使得别人送东西给他,倒似无形中给予了宋师一项重任,好意被他的郑重而加倍放大,这样的老先生,能不可敬吗?
更令人难忘的是,这位学生还写道宋老师回馈香烟给他,“用报纸包好的十包散装着的香烟给我。给我的同时,他却兢兢业业教导我说:烟,还是少抽为好,既然你已经不能不抽,就少抽,抽好一点的。”宋师固然没有大义凛然、厉言疾色痛陈抽烟之害,但想必这位仁兄以后抽到香烟必然感念师恩,感念师恩必然少抽烟或者抽好烟,甚至不抽也有可能。
对于学生,可谓倾注了全部心血。从没人见他在课堂上对学生怒目过,而学生却很尊敬他,他无职无权、无财无势,学生的尊敬,也并非因他的白发,而更多是被他的严谨、认真所感动、震撼。有位学生回忆,当她打电话给宋老师时,宋老师告诉她:“我正在备课。”学生很奇怪:“您还需要备课?”言外之意是,您是一位上了三十余年课程的老教授,难道还需要在上课前郑重其事的备课?然而事实确是如此,他的每节课都注入了最新理论成果,从不固步自封;除了常规的备课外,学生的作业他也提前认真阅读,细致到标出甚至改正平仄不对的字。看到他朴拙有力的字迹出现在学生或许不那么认真完成的作业上,学生们明白了什么是学无止境,什么是高山仰止。对于年轻的教师,宋老师此举的意义在于,对于学生,或许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的言传身教,比批评和惩罚,更能让他们向善。
他对人是如此的谦和,一生淡泊,不计名利,不与人争,而在学术上却像换了一个人,决不迁就、盲从,可谓是一个学术“怒汉”,尽显书生的血性。
他从事戏曲写作教学有三十余年,从创作到理论、从课堂到实践,孜孜不倦地探求戏曲写作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富有成效的教学体系。他“只问艺术是非,不计时潮毁誉”(陈多先生语),坚守一个理论者的良心,不虚美,不隐恶,不盲从,对于不知名作者的作品,他从不因人废剧,对于一些久负盛名的剧作,他也能排除众议,独出机杼。他专程拜访了已经缠绵病榻的徐进,并特意表达了对他所创作的《红楼梦》的敬仰。对于一个快要被遗忘了的自学成才的剧作家,收到来自学院派的肯定,那将会如何照亮他的余生。而对于一位在当下享有盛誉的剧作家,宋老师也直言了对他剧作的批评和建议,至于对方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码事。如对于集诸家赞誉于一身、几成定论的京剧《沙家浜》,他指出其在情节布局上以郭建光为中心人物是大误,认为逊于原著沪剧《芦荡火种》,,对于同样集美誉于一身的京剧《曹操与杨修》,他也指出剧中有“一些不小的疏漏,如情节不合生活逻辑和人物身份,结构不严谨等,以致部分地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其观点的正确与否,此处不加置评,单这种勇气和直言,
陈多先生曾赞赏他“排除一切多余顾虑和私心杂念,唯以探索戏曲创作规律为目标的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也正如此,他的文章才能在当前戏剧批评因日益陷入‘炒作’、‘跟风’等泥淖而不学少术之时,给人以空谷足音、跫然而喜之感”。可以说,在浮躁的学术泡沫的大海中,宋老师像一个安静的智者,洞观一切又不动声色,他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不大,但绝对具备穿透力。他自己在告别讲堂的研讨会上也说,从事戏曲写作教学,就像“在汪洋大海中划着一艘小船,寻找喜欢戏曲的孩子”,人如其言,有点像殉道者。
卸下教学重任的宋老师,似乎松了口气,可以陪师母四处走走、游游,可以颐养天年了。可他闲不下来:当他得知有位老先生编了本《成语韵编》,且此书对于学生戏曲写作大有裨益后,又多方奔走和呼吁,促成了此书的出版。他在理论道路的步伐也没有停止,先后又出版了《折子戏欣赏》、《名伶名剧赏析》等著作。他还带领学生创作了多个戏曲剧目,出版了《师生戏曲集》,内有多个剧目上演。这令大家刮目相看,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宋老师:除了能教书能理论,他还能创作能文艺。
正当大家为宋老师越活越精神,越活越洒脱而感叹时,2012年年初,大家得知了他患了肺癌,且已经骨转移。熟悉宋师的人都大为不解,像宋老师这般温和的好人,像他这样不抽烟的人,怎么会与肺癌这种恶疾遭遇?
而他留在学生们、同事们印象中的,仍然是一个不温不火,恬淡自如的宋老师,在向人讲述病情时的淡然,简直像在讲述他人的故事。而关心他、为他着急的人,也产生了错觉:一定是医生的误诊,一个晚期的老人,怎么能有如此的心境?大家也都相信,如果这种恶疾真的能被人体所控制,那一定发生在宋老师身上。
在这里,他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脊梁��有多少不曾为他人弯下的脊梁,在病魔的打击下溃不成军。而宋老师真有点“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的泰然。他不慌不忙地履行着他病中的计划,每次来校,均会给学生、同事带些馈赠的书籍,每次他都淡淡地说“我以后用不着了”。接受他的馈赠时,内心极知是告别,面对这位坚强的老人,我们又怎能不勉强作笑。即便是在他化疗期间,他也同样克己、坚忍,我们每次去探望他,无论他还是太太,均衣着整洁、头发齐整。对于登门探望者,他们总是亲身倒茶切水果,又亲自送至楼梯口,再三对探视表示感谢,表现出来的善良和至诚,几乎让人不忍再去叨扰,!
今年暑假,是学生和同事最后一次去探望他。他虽然消瘦了很多,但精神不错,意志坚定,之前他发来的短信也有“挣扎努力求生”之消极语,看到他的人,大家放心了不少,以为医学的奇迹就要出现,超高温的夏天都挺过来了,今年秋天定是无虞的。谁知九月的第一天就传来了噩耗。
想来人生有生老病死,生最长,而与老病死并举,也许只有老病死,才知生的意义,不在于为己,而在于为人,宋老师这个“人”字,无疑写得端正大气,是我们的榜样。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愿宋师在天安息!
(作者系宋光祖学生)
(编辑:榕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