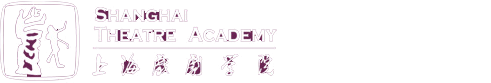这句话是张金娣教授说的,记得那是2012年的某一天,胡导老师又住进了第六人民医院16楼的病房,我和张金娣、万黎明去看望他,当时他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似乎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但他仍旧谈笑风生,嗓门很大的和我们探讨教学问题,他甚至毫不忌讳的大声说:“我要死了,但是你们放心,我是高高兴兴的死的!”出了病房,我们都不说话,都在避讳说出那个不祥的最后结局,这时,张金娣突然轻轻说了一句:“没有他,我们会寂寞的……”。沉默中,医院长长的小道上静的可以听见我们的脚步声。
过去总觉得胡导老师的名字有些怪,一般从事艺术工作的,总要起个响亮一点的名字,好让别人记住,可“胡导”这个名字似乎有些自轻自谦,好像没把自己太当回事。听说一件趣事,不知是否是演绎,文革前他带学生去大连演出,剧场门口来了一对男女,男的似乎想买票,女的却说:“你看那个导演的名字——胡导,能导好吗?不看了”。每当人们打趣的说起这件事,胡导老师不分辨也不解释,只是轻轻一笑。
第一次认识胡导老师是在1984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大学毕业刚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报到,走进办公室正赶上开会,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正在对全系教师讲话,我正茫然的看着一屋子不认识的人,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建平,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导演系老师了,暑假里多看书,有空我们聊聊”。自此,我就认识了我的系主任——胡导老师。时间长了,胡导老师年纪也越来越大,在背后,系里老师就逐渐用“老爷子”这个亲切的称呼来称呼他。可是当着他的面,还是要叫他“胡导老师”,因为大家知道,老师这个称呼是他的骄傲。
老爷子教学极其认真,记得为了说明“规定情境”,他看见学院道路上正在挖坑施工,竟跳进坑里,对学生解释情境突然改变对人物的制约作用,那时他72高龄;记得导01排演毕业剧目《萨勒姆女巫》,邀请他做指导老师,他每天必到排练场,督促学生做人物小品,直到演出圆满完成,那时他已90高龄;还记得他坐公交车赶到学校,端坐在在办公室看了一上午我的导演作品碟片,那时他已91高龄;最不能忘记的就是每到学期结束,他不顾劝阻,杵着拐杖,一步一喘地挪到四楼黑匣子看学生作业的汇报,最后一次来到黑匣子的他,那时已92高龄;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提出给他一个新的本科班,他要实现他的教学理想,那一年他已93高龄……。老爷子不仅关心教学,而且勤于笔耕,几年下来,用一台破电脑已经写出了三本导演表演理论专著,想想老爷子每天在陋室里佝偻着身子敲键盘,真令我辈汗颜。
老爷子身上不仅有着蜡炬成灰的教师精神,更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在他的一本书里,由于专业的关系提到了当年一位炙手可热后来成为阶下囚的人物,从专业出发,在他笔下自是褒扬多多,谁知到了出版社责任编辑那里,出于有关部门的有关规定要让他做“技术处理”。这本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一般人都会顺从那种不能明说的“规定”,改了就是,毕竟出版是大事。可是老爷子竟执拗的不肯修改,坚持说:“她就是个好演员嘛!为什么不实事求是!我不改!”可是不修改便不得出版,这是人家的规定,于是本该早早出版的那本专著竟被出版社束之高阁,过了很久做了“技术处理”才到读者的手中。老爷子一直为此事闷闷不乐,好几次对我说:“她就是个好演员!不能因为她后来不好而否定她的演技!”
缠绵病榻的老爷子仍旧那样激情四扬,见面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最近导演系教学情况怎么样?”语气中没有询问,而是急切地催问。每次去看望他,总要把系里的情况和学院的近况告诉他,本以为介绍一下情况就行了,可他却要详细问到每一位老师的教学情况,某某老师教学情况怎么样?最近是什么单元练习?教学有什么新的问题?毕业班排什么剧目?哪位老师导演?临别时,他总有一句话是要说的:“导演教学要发展,不能停留在过去”。那种精气神让我感觉他还会走进我们的课堂。可我每去一次,都可以看见他的逐渐衰弱,开始时可以在病房里慢慢走动,神采飞扬的说那些过去的趣闻轶事,还可以戴着假牙吃几块我专门为他烧的红烧五花肉;又去时,已经很少起床,话也少了起来,假牙也不带了,我带去的红烧肉只能含在嘴里品品滋味;再去时,那碗红烧肉只是象征性的给他看看,饱饱眼福……。最后一次去看他,我什么也不带了,因为他早已什么也吃不下,病床上的老爷子明显消瘦,原本丰满的双颊已经塌陷,只有眼神仍旧闪着生命的光芒,他望着我虚弱的说:“这次我真的要死了”。我喉头紧锁,竭力控制自己不流出泪水,反而语气蛮横不讲理地大声对他说:“胡导老师,您不能死,老师和学生们还等着给您过百岁呢,离中秋节您的生日没有多久了,您要坚持,您不能让我们失望啊!”老爷子看着我,好久好久,脸上浮出浅浅的笑容,轻轻地点了点头。可是,老爷子还是让我们失望了,他没有能支撑到我们盼望的期颐之年。
有件事让我遗憾又不遗憾,每次去都想给他拍几张照片,让他的模样永远保留下来,可是看着他逐渐衰弱,竟没有勇气拿出相机。现在想想这样也好,就让他精神矍铄的模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吧。
亲爱的胡导老师,让我悄悄地对您说一句:“您不在了,我们真的会很寂寞……”。(文:李建平 编辑:榕树)